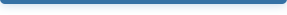近代史研究所“十七年”间的故事,现在很少人讲得完全了。我虽有16年时间担任研究所的负责工作,又在“文革”前进所,虽耳闻一些零星故事,也不能系统讲清楚近代史所与“十七年”史学的故事。我长期以为,近代史所的文书档案因“文革”动荡,早已不存于世,不免生有遗珠之憾。现在读了赵庆云的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方才知道他找到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文书档案,加上科学院的早期档案和个人日记以及回忆等资料,努力复原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历史,真是可喜可贺!
近代史所的历史,如果加上前身,已经过了70年。它的历史,它在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和作用,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史学界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包括今天在事领导诸公在内。这些已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成为一门学问了。赵庆云的研究意义也在于此。
70年前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科学院建立,在史学领域,为什么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而不是首先建立历史研究所,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范文澜作为延安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他的史学专精在中国古代史,他下的功夫也在《中国通史简编》,虽然他也编著了《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什么他坚决主张中国科学院首先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我想这要回顾延安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郑重地提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他认为党内的学习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认为这是极坏的作风。谈到研究历史,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为了克服党内学习方面的三个弊病,毛泽东有三个针对性的提议。在研究历史方面,他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它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都是党的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学习和贯彻这三篇基本文献,极大地改善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提高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三篇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毛泽东关于研究近百年史的提议十分明确、具体。我们知道,范文澜在延安与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上是有交流的。范文澜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心悦诚服的。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的这个提议,就是范文澜坚持在中国科学院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根据。
我在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报到后两天就被所里派去参加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任政法组秘书。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国家之力举办的一次最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包括了文、史、哲、经以及自然科学各学科。我看到范文澜所长、刘大年副所长都是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很活跃。在政法组,我看到刘桂五先生,也是很活跃的成员。刘桂五那时是近代史所的学术秘书,地位很重要。我在会上认识了安藤彦太郎先生和岸阳子小姐,他们两位后来结为夫妻,刘大年是他们两位的红媒。
说起刘桂五,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某年我在京西宾馆出席社科基金评审会。那里还有两院院士遴选会议在同时进行。我刚进房间坐定,就有人敲门。来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一位老研究员。他进来对我说,看见社科基金的评审会在这里,他猜想一定会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人参加,到会务组打听,知道了我的房间。他一进门就说,看见近代史所的人很亲切。他告诉我,1951年中国科学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报告人是近代史所的刘桂五。他说,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举手投足,他都印象深刻。老院士还说,近代史所在科学院的地位极其重要,很不一般。刘桂五不是近代史所负责人,科学院请他在全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这件事情在今天不可想象。他说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与我的了解是相同的,可见这位老院士的记忆是准确的。
赵庆云早些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毕业后留所工作,很有成绩。他现在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学有所归。
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与“十七年”史学的关系,不是仅仅一个近代史所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史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很有理论意义。我觉得,他的研究值得学术界关注,特作赘言如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