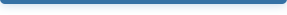由我国著名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老舍研究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关纪新先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最终成果完成。2014年6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举办“《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成果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致贺词,并与来自文学界的梁庭望、曹顺庆、徐新建、李怡、李玲、逄增玉、赵志忠、李红雨、徐文海、刘淑玲、吕微、郎櫻、尹虎彬等数十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主持。《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在学术史上首度完整地对满族小说的通盘成就做出了梳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成果之一。《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将满族小说创作的总体业绩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流变相联系加以考量,与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汉族文化而又注意葆有自己的审美特征相联系加以探究,在学术史上首度完整地对满族小说的通盘成就做出梳理。全书分为若干主题,分析了满族小说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整体展开过程中的表现与意蕴,并对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二者的相互关系做出深入分析,广泛调动多学科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满族小说在中华文化大格局中存在与呈现的能量,给与了比较完整深入的挖掘和描述。本书旨在展示出满族小说与汉族小说的“同”和“异”,既认定汉族文化给予满族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又要看清满族小说创作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审美差异,从而阐释出满族小说创作回馈给中华文化的多重价值所在。
关纪新先生作为满族人,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抉择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满族入关不久,即全面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一决策,一方面使满族获取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却也使满族作家失去了运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写作的机会。满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却仍保留了自身的民族性格,并形成了风味独特的京旗文化。虽然满族作家在写作时大多使用汉语,但他们的民族性格、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特点无不渗透于作品当中,由此形成满族小说有别于其他民族作品的重要特征。
关纪新先生说,满族小说以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为中华文化增加了丰富的色彩,也为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关先生指出:“从17世纪前期满洲民族崛起于东方,到20世纪该民族运交于华盖,满人始终处在国内外民族关系的风口浪尖,大起大落大跌大宕的沧桑经历,教他们比其他民族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峻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满族的小说作品,不单向世间原原本本地描绘了自我民族的本来面目,有利于兄弟民族对自己的了解和尊重,还十分动情地疾声呼唤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平等与和睦相处。满族小说从清代到现代不同阶段的此项书写,在相应历史时期,都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表达中,占据重要位置。我们今天也当充分肯定满族小说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当中,所正确表达的民族理念。”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满族小说创作领域代表性作家、批评家的基本扫描与个案研究。其中,重点关注的作家包括:清乾隆年间的曹雪芹、弘晓、敦敏、敦诚、永忠、和邦额、庆兰;清代后期的文康、西林太清、裕瑞、石玉昆;清末民初的松友梅、冷佛、穆儒丐;20世纪的老舍、王度庐、赵大年、叶广芩等。关先生对他们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创作性劳作,均给予细致的分辨和诠释。
第二,剖析满族小说的产生及其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满族全民对于叙事文学异常偏爱(萨满文化中瑰丽多姿的叙事传统以及民间长篇“说部”宏大叙事的艺术习尚),与清代满洲全民族对“稗史”类作品的亲近(明末清初满族对汉族历史小说的翻译热潮、清代满人创作小说的迅猛崛起、“子弟书”对中原长篇叙事韵文缺失的填补与丰富),是对汉族文学一向以诗文为“正宗”而斥小说写作为“不登大雅”的积极反拨。在中华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各领一代风骚,满族则对清代小说的勃兴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的审美习尚与满族的审美习尚密切相关。
第三,对满族小说风格的研究及其文化底蕴和渊源的挖掘。满族小说作家在文学的雅俗关系上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俗”——即在通俗平易的描述中见出大“雅”的情趣与追求,通过大俗来接近大雅。同时,满族小说家秉承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在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举重若轻、闲适优雅、幽默调侃、泪中见笑等气质习性,为中华文化的整合构成输送了诸多重要的新鲜元素。
第四,充分注意满族作家们写小说,重在表现民族精神传统,体现出诸多与汉族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红楼梦》体现出的进步的女性观,与汉族一些文学将女性认作“祸水”截然相反,是和满族萨满教传统中多推崇圣洁女神形象相关,也和满族民间长期保持尊重女性的习俗有关。
第五,重视满族小说的悲剧情怀与文化积淀。满族小说作家在创作中,擅长以悲天悯人的人生况味来描写本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个人胸中的块垒。曹雪芹的《红楼梦》即以“悬崖撒手”的决绝谱写了“盛世之哀音”,打破了大团圆式的“否极泰来”书写模式;清末民初的满族小说家和后来的老舍,更是不断推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深入状写历史的沧桑更迭与个体的生存无奈,使中国小说有力地突破了中原叙事模式中的“大团圆”书写。
第六,探讨满族小说家在创作中,充分运用和信赖口语白话,为汉语的白话文写作展示了广阔前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有效地借助了清代及近代满族小说家们的写作经验。
第七,对满族小说与北京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予以辨析。满族小说作家以北京为写作“热土”,作品大量呈现“京味儿”特色,为我国“京味儿”小说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八,关切到满族作家的小说写作,往往与百姓喜闻乐见的其他门类艺术相结合,体现出小说与北方曲艺、戏曲等样式的有机合流。
第九,论述了满族小说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现代转型。长期以来人们有个错觉,以为腐朽的晚清不可能出现新鲜的文化种子,而事实上当时的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因子已有呈现。清末民初满族报人小说家们在传播新思想、开拓言论空间上曾经明确发挥作用,亦以创作实践呼应了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
第十,诠释了满族小说的当代发展态势及其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关系。通过对于当代满族小说地图的描绘,发掘其作为中华文学总体的一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补苴罅漏、补充输血的功能。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满族文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历史作用。满族这个民族虽然出现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却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民族,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而且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有着非同凡响的诸多建树。满族本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以原始萨满文化为基本信仰层面的一个民族;随着17世纪前半叶进入中原腹地建立清王朝,中原文化由外到内对该民族做了一番洗礼。然而,满族在形式上接受汉族文化之时,却在文化的某些内核方面顽强地保留了原本独特的东西,其中包括在文学上面(特别是小说创作方面)有胆有识地保留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趣尚和价值标准。这些趣尚和标准,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并非是消极的,例如它强调文学是用以表达人们性情的,注重保持文学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鼓励文学启用人民群众每日每时所使用的口语白话,推崇通俗晓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均为中华文化的推进与繁荣,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和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演进,做了一定的先期准备。这些趣尚和标准是满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因而发掘其渐被历史烟尘所湮没的文化因子,及考察这种文化因子如何融入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中,有意义。
二是认识满族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无论是就清代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来说,满族文学都是与汉族文学走得最近的一种民族文学,以至于有些论者容易轻易断言满族文学缺少个性,只是汉族文学乏善可陈的附丽物。本书提出的重要论断之一在于,满族文学(特别是满族小说)并非是汉族文学的简单翻版,一方面它确实受到了汉族文学的深刻影响,连表达形式都是汉族样式的,另一方面,它又没有为汉族文学彻底“同化”,依然保持了自己一些健全的特殊的因素,积极地作用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体现在书面文学上面,不仅强调着“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且以文言文书写,并伴以大量堆砌佶屈聱牙的经典来引为高雅,使满族这样的文坛的“后来闯入者”相形见绌。尽管明代以来白话创作渐趋兴盛,但是作为文学正统的诗歌散文,依然占据主流和正统位置。为了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满族作家们抑短扬长,在用自然流畅的大白话写人的性情、写身边的民俗生活、平凡故事方面别开生面,开辟了新的文学天地。从曹雪芹到文康再到老舍,满族小说家们有着自己的“别样追求”,也完成了自己的“别样奉献”。
三是认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学关系。不同民族在文学与文化上的近距离交往,古已有之,清代的满汉文学暨文化交往,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在满汉文化交往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满族曾经大幅度地接受汉文化,基本上放弃了自身的民族语言,运用汉族文学样式来写作。但是,文化史的演进道路又是错综复杂的,清代的满洲民族优秀作家们,于无奈之下,却终于走出了与汉族文学“和而不同”的艺术路径,为后世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对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课题深入思考的空间。由此可以想象的是,在民族文化上的近距离交往过程,弱势民族并非总是毫无作为,只要充分焕发起自身的个性期许与聪明才智,调动起自身文化深层的生命活力,扬长避短,仍然能够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新的自信和自立,从而与其他民族文化去做彼此有益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