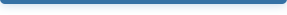■《古典学研究》创刊号
■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
■顾枝鹰、张培均团队翻译的《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
■贺方婴专著《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上的奥德修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外文所”)拥有深厚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传统。自建院初期,学者们便开始了对荷马史诗、希腊神话以及古希腊戏剧的翻译与研究。岁月流转,学脉绵延,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不断深化,一批批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2023年,外文所成立古典学研究室,为推动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研究核心的古典学赋予了崭新的活力。近日,记者走进外文所古典学研究室,采访研究室负责人贺方婴及该所助理研究员张培均和顾枝鹰,围绕我院古典学传承脉络及古希腊文学在现代世界的意义等话题,进行多维探讨和交流。
“学脉”传承推进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能跟读者分享一下你们投身古典学研究的原因和经历吗?
张培均: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一年级时我主修社会学。即将进入大二时,我在学校草坪看到第一届古典学实验班的招生通知,看到大大的海报上同时印着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画像,觉得这是自己想学的——学贯古今中西,想想都令人激动!这算是我的初心,初生牛犊不怕虎。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非常遥远的目标,需要用一生去追寻。本科期间,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汉语上,并首次接触到古希腊文学。经过三年学习,我有了比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本科时的学习谈不上学术训练,但古典班的两种做法对以后有志于学术的学生非常有帮助:一是注重语言上的训练,除了西方古典语言,还有古代汉语;二是注重中西方经典文本的阅读。
我觉得不管以研究中学还是西学为主,对东西经典有个大致的了解非常有用,能使自己的思考始终处于思想的张力之中,提醒自己不走极端。大学毕业前,我投笔从戎,参军两年。退伍后,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阶段,我主要研究古罗马作家撒路斯特的作品。我在博士阶段才真正深入研究古希腊文本。
顾枝鹰:我在高中毕业后开始自学拉丁语。原本是出于好奇,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就对拉丁语经典作品逐渐产生了兴趣,为了理解原文,就更有学习动力了。用1年时间学完语法之后,就开始自学古希腊语,同样使用了以阅读经典为目标的教材。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拉丁语文学,尤其是西塞罗的散文。在古希腊语文学方面,我与张培均老师以及其他博士同学一起翻译了《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这是目前汉语学界译介过来的最全面、系统、详细的古希腊语语法工具书。
贺方婴:和两位青年学者“规整”的求学经历不同,我与古典学的结缘是“跨界”偷学的结果。2001年,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刘小枫老师在哲学系首次开设经典文本的导读课,由他带读柏拉图《斐多》、尼采《敌基督》、黑格尔《历史哲学》,当时闻风蹭课的学生很多,校内校外的都有。刘小枫老师每次上课6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中间留出1个小时吃饭时间。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从白天到晚上的高强度讲和学,大家都亢奋得很。那时候老师和学生的读书状态都很“疯”,可能正是阅读经典的魅力。
从那时起,我跟随刘老师从最基础的两门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起步,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地每天背诵古希腊语的词根、变位。当年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喝水练习发小舌音,互相帮助校对希腊文翻译,帮导师整理、翻译古希腊语学习资料,下晚课后,我们在中山大学的草坪上高声朗诵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句。20多年过去了,很庆幸自己选对了问道古典的学问之路,内心一直充满力量,很踏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古典学研究室的具体情况如何?在研究室成立之前,外文所的古希腊文学研究情况是怎样的?
贺方婴:古典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于2023年12月14日,是国内第一个古典学研究实体机构。古典学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国内外很多古典学研究同行的祝福和鼓励,王焕生老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激动,他说:“古典学终于有家了!”我的导师刘小枫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是当之无愧的国家队,实实在在地推进古典学学科建设。没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办不到。”老一辈古典学人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有太多的殷切期盼。可以说,古典学研究室的成立是政策支持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响应和切实贯彻“两个结合”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结果。我院近几年对“冷门绝学”越来越重视并积极扶持,外文所的领导班子也非常重视以古希腊罗马研究为核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
程巍所长专门与我们团队一起制定了“五个一”的古典学学科发展计划。目前我们所正逐步开创“一室一会一刊一库一中心”(即古典学研究室、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古典学研究》期刊、古典学综合数据库和院级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五位一体的学科格局。借助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东风,我们未来将与国内外古典学同行全面展开学术合作。目前,我们古典学团队的特征是年轻化、专业化。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展现出勃勃生机,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外文所的古希腊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建所之初。在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研究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罗念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古典学学脉奠基人,是第一位留学希腊的中国人。归国任教后,他便着手翻译古希腊的悲剧。目前,我们阅读的荷马两部史诗,古希腊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肃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剧作,都以罗老的译本流传最广。令人感佩的是,罗老去世前,仍然在病床前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生前《伊利亚特》还没有翻译完,后面还有一半篇幅是由他的学生、外文所王焕生先生接续完成,王老今年也已经85岁高龄了。
顾枝鹰:高翔院长提到过“学脉”。外文所的古典学学脉一直在代代相传。从罗老到王老,再到贺方婴老师,再到新一代的张培均老师和我,我们一直在延续学脉,接力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一方面是经典文献的翻译,另一方面是古典语言的工具书编译。目前,贺老师正在修订王焕生先生的《奥德赛》译本,同时补充大量学术性注释。
在古希腊语工具书方面,外文所可以说撑起了大片江山:罗念生先生和水建馥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了一本300万字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受限于排印技术和编辑条件,这本书直到2004年才正式出版);除了之前提到过的《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我们还在进行《古典学译名手册》的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内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学术史?
张培均:刚才贺老师谈到,外文所的罗念生先生是国内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其实第二代古典学人王焕生先生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也为古希腊文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罗老到王老,再到古典学研究室的成立,外文所在古希腊文学研究领域已迈出巨大的一步。另外,外文所主办的《古典学研究》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的古典学专业期刊,自2023年创刊以来,已发表众多关于古希腊文学研究的优秀论文。
当然,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在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尽管此前国内古典学研究领域已做了诸多基础工作,但影响力的增强是近年来才逐渐显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大型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约750种,为国内古典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古典学实验班,多年来也培养了不少古希腊文学人才。
正本溯源开展古希腊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咱们古希腊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贺方婴:今年夏天,我和王焕生先生约定,要在他和罗念生先生的译本基础上,继续完成荷马史诗详注本的翻译和疏解。至于对荷马史诗的研究推进,我2022年出版的《荷马之志》只能算是一个起点,希望接棒前辈学人的志向,完成史诗《奥德赛》研究三部曲。
张培均:我目前在翻译希罗多德的《原史》一书,并在译本中加入注释。现有的中译本多将其译为《历史》,然而我更倾向于将其译为《原史》。因为这一译法更能体现其探究的含义,“history”一词在希罗多德的语境中并非指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而是指对人世间城邦兴衰、命运变迁规律的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古希腊文学研究需要重视哪些方面?
张培均:注释对于经典文本的精读非常重要,鉴于单一译本可能无法充分阐释原文的丰富内容,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借助前人的注释解读文本本身,而非简单地将西方理论套用于文本,或以现代视角重新构建古代文本。古典学研究要求我们充分理解作者的原意。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的预设和偏见。但在研究古典文本时,若不尽可能地避免将个人的现代观点代入其中,就会错失作者的原意,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所谓新的见解就不可靠。因此我认为,研究者应当努力理解作者的原意,而非仅仅从作者的著作中寻找语句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深入理解古代伟大作家真实的所想所写。
顾枝鹰:张老师刚才提到他在翻译希罗多德的作品。其实之前国内至少有过两个译本,之所以张老师还要重新翻译,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前两个译本是从英语翻译来的,而张老师是从古希腊语校勘本翻译的。很多英译本会丢失原文的精妙意味,而一些马虎的中译者甚至连英译本都无法忠实。我与张老师等学友一起翻译《剑桥古典希腊语语法》《拉丁语语法新编》,目的之一就是呈现一种忠实于原文的中译风格,促进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传世经典的中文翻译工作。精良的中译本可以促进汉语学界对原文的理解,有利于古典学学科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古希腊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张培均:国内的古希腊文学研究,在翻译层面已经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大部分重要作品都有中译本。但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完成从有到好的转变。现有的许多古希腊文学作品的中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从古希腊文翻译成英文会损失一点意思,再从英文转译为中文又会损失一点意思,而且中间可能会因为对英文的理解偏差而出现额外的错误。尽管从古希腊文翻译也可能存在错误,但是这样至少没有隔一层,所以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古希腊文语言精密,如果不吃透句子,就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翻译与理解。
顾枝鹰:纪事性文本需要追求精确性,哲学文本更是如此。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话为例,比较常见的译文是“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但更加符合原文的中译文可以是“所有人在本性上都欲求知道”。显然,这两个中文表达在结构上存在不小的差异。前一种译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十分显著地有益于中文版读者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古希腊文学研究具有怎样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顾枝鹰:现代西方文明由西方古代文明演化而来。后者在某些方面可能放大了西方古代文明的某些特征,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可能偏离了西方古代文明的某些传统。在当代中国,我们所持有的许多观念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影响。因此,为了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文明,我们有必要去探究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典学研究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可以用“文明互鉴”来概括。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品与中国古代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有可以互鉴的地方。西方古今之间存在断裂,但现代中国主要受到现代西方影响,研究古希腊文学有助于正本清源,有助于从中西方的古典作品中汲取智慧以矫正现代问题。
凝心聚力建设古典学研究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我院设立的“绝学”项目将古希腊文学纳入其中。您认为这给古希腊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机遇?
贺方婴:虽然2009年我院便将古希腊文学设立为“绝学”项目,但是其发展并不理想。随着王焕生、陈中梅等研究人员的退休,外文所的古希腊文学研究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转机出现在近几年,自高翔院长上任以来,他对古典学给予了非常大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这对学科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高翔院长今年6月12日来外文所调研时,曾专门来到古典学研究室探望我们团队这些青年古典学者,并翻看了最新一期的《古典学研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高翔院长翻阅我们室编的“经典与解释·古今丛编”古典学研究系列丛书时,鼓励我们把这些冷门绝学类的书一直做下去,并且深有感触地说,“社科院就是要做其他高校做不了的事”。他鼓励我们要有建设国内古典学研究重镇的长远规划和目标,这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年来,外文所为古希腊文学研究做出了哪些努力?
贺方婴:老实说,我们所上上下下都在扶持古典学研究团队成长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是科研岗位的研究同行,还是行政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均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助力。令我难忘的是,去年在《古典学研究》创刊之际,外文所科研处的张文博老师为了尽快拿到出版许可证,赶在下班前前往新闻出版总署取批文。拿到批文后第一时间就向我们传达了这一喜讯。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可看到整个研究所对这一学科寄予的厚望,更不用说办公室、财务处等行政部门的老师们有无数令我们倍感温暖的工作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咱们院之外,还有很多学校在进行古希腊文学相关研究。您认为,相较于他们,外文所的古希腊文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贺方婴:我们研究团队的显著特色在于成员的年轻化与专业化。在人才引进与招聘中,除了专业要求之外,我们特别注重年轻学者的家国情怀,对自身文明的关切与责任感。因此,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推动年轻一代对伟大经典的重新理解。我们团队中青年学者都是从做学问之初就专注于古典学核心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他们未来的研究道路势必更为宽广。在刘小枫老师的加盟支持下,由古典学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学研究系列丛书“经典与解释·古今丛编”“经典与解释·古今论丛”已于今年6月出版首辑。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空间和舞台交给新一代的古典学人。
重读经典彰显古典学研究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古希腊文学在我国不同时期的接受和转化?
顾枝鹰:外文所的古典学研究,在学脉和源头上充满了对中华文明的关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在研究古典学时,我们并非简单地承袭西方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理念,而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进行损益。以罗念生先生为例,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古希腊战争故事,有着当时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现实背景。他翻译这些文本的目的是唤起中华民族积极抵抗的精神。我们在今天同样会根据中国当代文明的具体需求来选择那些与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最相关的特定的经典。至于古希腊文明的接受问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典学研究视角来看,“接受”研究目前应当被视为对文本研究的一种补充,不宜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现代技术,例如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影响?
贺方婴: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古希腊诗文中的核心论题。在古希腊肃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中著名的“人颂”,面对自然界强大的力量,人何以自认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战胜一切?那是因为人类凭智慧发明了各种技艺,以此弥补人的天然不足。比如面对寒冷,动物有皮毛,人类则制作衣服保暖;面对肉身无法抵抗凶猛的野兽,我们发明了各种武器……可是肃剧诗人索翁却是以一种悖论式的语境把这一段“人颂”放进了讨论自然礼法与城邦律法之争、执拗天性与命运之争的《安提戈涅》中,是不是别有深意?古希腊人之所以将自然和技术放在一起对比,是因为希望探讨出自自然之手与出自人手的造物谁更加高明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生活充满科技感,人之脆弱可能是我们存在过的唯一凭据。人与机器人的唯一区别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脆弱——情感脆弱、身体脆弱……或许人的不完美和终将一死成为人类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这很有些吊诡的意味。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应当警惕科技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整体性伤害。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向我们推荐一部您最喜欢的古希腊文学经典作品吧。
贺方婴:我推荐大家去重新阅读荷马的两部史诗,十年读荷马让我意识到这位伟大的古代诗人对于人世的理解,抵达了一种现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深度。
张培均:我推荐希罗多德的《原史》。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多彩,是对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一项探究,给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带去异域的事物和观念。他所处的时代,希腊正发生巨大变革,两场大战正重塑着希腊智识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希罗多德自己曾驱逐家乡的僭主,也参与过雅典人的殖民计划,还曾周游各地,经历非常丰富。希罗多德的表达既非常严肃也非常戏谑,带着一点儿冷幽默。通过自己翻译,我发现希罗多德有一种幽默感。他还是个非常隐微的作家,比如书中会有不少类似“我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不说”这样的表述。希罗多德想告诉读者,他知道的远比他写下来的多,这也要求我们更仔细地去阅读他的著作。
顾枝鹰:首选的话,应该是刘小枫教授编译的《柏拉图四书》。柏拉图确实让我看到了许多令我惊讶的东西,他不仅是我最喜欢的古希腊作家,也是我最喜欢的古罗马作家西塞罗最推崇的古希腊作家。《柏拉图四书》的译文准确、优美,而且对话情节引人入胜,应该能够激发读者对古希腊文学和古典学的兴趣。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